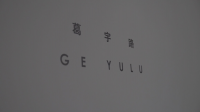如果不了解葛宇路的故事,初见他这个人,会觉得他身
上并没有“艺术家”这个标签下的某些特征,他没有留长
发或蓄胡须,也没有任何架子,就像是平常可以在任何
地方结识的新朋友。直到加入和他的交流开始,才发现
这个人真的不太一样。
跟葛宇路聊天是一件很棒的事,他会把你带进某个思路
和语境里,在那里阐述他的想法,与人对谈。尽管这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的话时常会触碰到他人的思
维盲区,有时干脆就逆着常理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
就想问什么是常理,什么是常?”
一个用自己身体发电给展厅和作品供电的行为艺术家,
也是一个用风机吹着一封信步行两周寄信的男朋友,还
是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一条无名道路的美院学生,他完
美的绕开了符合常理的行为方式,找到了他自己做艺术
的节奏,他自然清楚何谓常理。
在很多观众的眼里,他的作品似乎次次在触碰着我们熟
悉的所谓“常理“的边界。采访的时候他说“我要说不知
道有这个边界吧,显得挺虚伪的,但说有这个边界吧,
我又觉得其实也没什么边界,或者说它是可以打破的”
在东湖捞《东湖》
那年武汉东湖边的码头,葛宇路坐着拨通了当地某个潜
水教练的手机号,这是拒绝了他的一位教练提供的,拒
绝的理由是去外地打捞了。在电话里葛宇路跟对方解释
了来电的原因——希望他们能下潜到东湖底打捞一块公
交站牌,那是他的一件艺术作品。当时电话的那头又确
认了一遍需要打捞的物品,然后“噗嗤”一声笑了。
几个小时(天)前,他包船回到了湖中的那根用铁丝绑
缚站牌的柱子旁边,然而柱子上的站牌已经不在原处。
他找来拳头大的磁铁,绑上绳子,从船上伸进水底去捞,
很久之后也没有捞上来。游泳路过的大爷讲着几个月前
的故事:“那时候有几个小孩儿游泳过来,爬上柱子跳
水玩,那时候(牌子)就没了”。临走前大爷还说着“这
怎么找,找不见的”。
大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或者说觉得他办不到。这么个
牌子也不知道在不在柱子下的水底,就算它在湖底,也
只能用手在黑暗的水底寻摸,就算它在湖底,找到了又
有什么用呢?潜水的教练平时都是在水底寻找废弃的导
弹,或是打捞沉水的文物,遇上葛宇路这样“无理”的需
求也是头一回。
葛宇路知道自己这个需求是不合常理的,但那块站牌对
他来说真的太重要了,那是一块他在深夜的北京街头用
电钻一点一点钻开的“东湖站”站牌,站名跟眼前武汉老
家的这个湖名字一样,是他亲手绑在柱子上的,也是他
大学的作品《我在东湖的一米》的延续,是他这个人的
一部分。
跟教练的沟通花了几顿饭的时间,葛宇路讲述了他跟站
牌,跟东湖的故事,对方渐渐放下了戒备,并开始接受
这个不值钱的站牌对葛宇路这个思路清奇的青年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
不久之后,葛宇路学会了潜水,跟他的教练一起顺着那
根柱子潜入了漆黑的湖底。他身上佩戴的潜水相机从入
水开始拍摄了15分钟,之后他浮出水面,手里拿着那块
来自北京的公交站牌,蹲在柱子上的教练接过站牌,展
颜而笑。他的运气是不错的,这也源于他的“尽人事”。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水底,人的搜索范围十分受限,可能
离目标物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但还是会错过。很难想
象这样一块几十公分见方的铁牌子的落水姿态是什么样
的,落在了哪个位置,被多厚的泥所覆盖。无论是被游
过一大片湖面后爬上柱子的小孩取下来扔进了湖里,还
是说一阵大风大雨吹松了连接的铁丝,最后还是被挂起
它的人找到了。
葛宇路似乎对于寻求与各种职业者的合作有所偏爱,尽
管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有这样的偏爱。
从《东湖捞东湖》寻求潜水教练的帮助,到个展《葛宇
路》找自行车的改装爱好者,葛宇路似乎对于寻求与各
种职业者的合作有所偏爱,或者说,他对于领域跨得离
他越远的职业和工作方式越感兴趣,尽管他自己也说不
清楚为什么有这样的偏爱。对他来说,每一次跟不同的
人合作都是一次“新的打开”,因为每次他都会有意识地
去学习对应的专业技能。但他很清楚,对于他人既有的
领域,他就是个一入侵者,每个人听到他需求的第一反
应都是:你在开玩笑吧?其实他的玩笑跟幽默,都被放
进了作品里,而创作的过程是一丝不苟的,甚至有点
“轴”。
5月中旬,距离葛宇路的第一次同名个展《葛宇路》开
幕还有一周多的时间,辗转了燕郊的几家自行车行之后,
他碰了一鼻子灰。没有任何一家店愿意帮他改装一台能
从供电变蓄电的助力自行车。“我们有这款,不就是发
电机给车供电吗?”“不是的,是我给发电机供电。”“那
不是反过来吗?”“对,就是反过来。”听完后,店家好
像有点生气。
燕郊捷安特店店家给他的第一回应是“你这我做不了,
我就是个卖自行车的,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听不懂的。”
但葛宇路也明白被拒绝的根本原因“其实他听得懂,但
他价值观上是抗拒的。”站在自行车店里的葛宇路很清
楚,自己的需求对于拥有电动自行车产品的店家来说,
是一次需要完全逆向思维且没钱赚的挑战,他们不会有
任何兴趣的。不过他还是跑遍了燕郊的自行车行。
后来帮他选车并改装好自行车的,是一位河南某县的中
年大叔,是个热爱机械改装的手工达人,葛宇路就喊他
“师傅”。自行车寄到后,师傅就发来了几条开箱组装和
讲解零部件的小视频,详细描述了自行车需要改装的部
分和成品效果。着手改装后,“大概一个中午就搞定了”
葛宇路说,“很快,非常快,我以为很难。”
但这个改装的时长已经证明了,其实并不难,他用来说
服自行车行老板的时间都比改装的时间长很多。
“我希望(自己)是可以完全被打开的,不希望有任何
限制,但我也很清楚自己有很多限制”
很显然,从第一个作品开始,葛宇路的创作都离“美术
馆”比较远,一方面是源于行为艺术对于创作环境的需
求,另一方面,是他更喜欢在这广阔世界里去表达,留
下痕迹。
对于葛宇路而言,用自己能量给作品发电,其实本质上
是利用自身运动所产生的能量,为同样是由艺术家自身
能量供应完成的作品在空间中展示而供电,在挑战人们
的观展习惯的同时,质疑了美术馆与画廊的固有属性——
连接上公共状态的能源供应的灯光打在作品上供人欣赏。
在画廊,大部分艺术展都会挂起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往
往拥有着独立的灯光,灯的高度会尽量贴近艺术空间的
挑高,以避免任何观众在凑近观看时因为灯光过低带来
的阴影;它们一般被挂在刚刚粉刷过的白色展墙上,各
自之间有计算考量过的间距,让观众在某一段距离能获
得最佳的观看效果;它们被设定成一种序列,让观众在
潜意识里便接受了艺术与自己日常生活的距离感——一
种被安排的孤立。
在葛宇路设置的展厅里,观众的出现和走动会触发感应
开关,点亮展厅里悬挂着用来播放他以前作品视频片段
的屏幕,电源是一块由他蹬车蓄电的铅酸电池。观众在
观看由艺术家在作品和电能的双重能量供应的展览时,
也能在电能耗尽时体验到艺术家的身体极限。
“我一天能发的电就那么多”葛宇路在直播骑行时对观众
说。其实在真正开始试发电骑行前他并没有料到,骑车
动能和电能的转化率是如此低,以至于试骑那天晚上他
走到三分之一的里程时还没有真正蓄入电能。
站在入夜的滨河路边,呼啸而过的水泥车卷起扬尘,葛
宇路跟师傅通了语音并更改了电池的设定,他已经清楚,
无论设置如何更改,电池的充电只有在轮胎转速达到一
定程度时才能实现,而在短暂的冲刺加速后,他已经气
喘吁吁。
虽然还没有完全放弃用纯粹骑行的方式来发电,但那天
开始,葛宇路应该也已经对自己发电效能的极限有了一
个预期,而如果要满足某个数量的观众能看完展览,他
可能需要三十公里从头至尾都在冲刺,这不是一个正常
人能做到的,更不用说还需要骑一台摩擦阻力非常高的
发电自行车了。
展览开幕前几日,葛宇路已经多次尝试了原地蹬车蓄电,
从掉电情况基本确定了每天需要上车发电的时长,再加
上从住所到美术馆的几次下坡冲刺,基本可以满足每天
30-90分钟的展览供应。为了尽可能让前来观展的人能
够看完展览,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原地空转的发电方式。
这也差不多是他的底线了。
5月22日一早,理了一个板寸的葛宇路把车子推出单元
门停好,打开了运动相机和手机直播平台,嘴里碎碎念
吐槽着并试图关掉直播软件自启动的美颜功能“好恶心
啊,这根本不是我。”
从早上9点多出发后,葛宇路一路休息了几回,期间吃
了两根冰棍、一顿盖饭、半个西瓜,还买了半框蜂巢,
最有意思的是,在皮村停车休息结束后,骑出去好几百
米了,他都没想起来身后背的大双肩包被落在了原地。
后来聊起来,他说自己经常会有注意力缺失的情况,有
一回离开家办事连家门都没关就走了,晚上回来才发现。
他自己形容说:“不是那种虚掩着,是大开着,有45度
那么大。”
下午三点半,历时近六个小时,骑行三十多公里的葛宇
路到达北京公社,第一时间把电瓶接入展场的装置,展
览顺利开幕。展出时长大约两个半小时,观众络绎不绝,
电池的最后一格电,在最后一名观众离开后刚好用尽。
前一天,他在家蹬了六七个小时才休息。
“艺术家是不应该有特权的”
展览开始后,除了美术馆的固定闭馆日,葛宇路几乎每
天都要发电,否则慕名而来的观众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漆
黑的展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已经逐渐适
应了每天的运动,心肺功能也有所提升。
6月中的某天,在燕郊的出租屋里,葛宇路一边蹬车,
一边看着电视上的艺术类视频节目,不知不觉聊起了作
为艺术家应该是何种样子。他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艺
术家是不应该有特权的”,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展开,但
这样一句话里似乎还藏着更多想要表达的内容。
“艺术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拥有一种精英的身份,或
者一种启迪的能力,或者他不同于大众,是高高在上
的。”这就是一种拥有特权的幻觉。然而葛宇路很清醒:
“艺术不是能用来“介入”社会的,艺术家也没有这个资
格用它来介入社会,它原本就存在于社会中,艺术家也
是社会的一部分。”
有一些艺术作品在完成后,的确和现有的社会规则会发
生大大小小的碰撞,然而在葛宇路看来这些碰撞是正常
的,任何人在与规则相违背时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不能说我这是艺术,是高高在上来介入的,你们不能
用平庸的法则来惩罚我。”无论是道德也好,法律也好,
一个作品产生了,艺术家都要接受社会的审判,“不能
说因为我做的是艺术,这种惩罚对我无效,他就要承担
这个结果。”
“懂不懂艺术都不影响这个惩罚机制,同样地,惩罚与
否都不影响这个作品的好坏。”其实葛宇路是在用这样
的信条来捍卫艺术。当“能挑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常常容
易被直接划分为“好的艺术”的时候,人们似乎很难对此
表示怀疑,如此一来,更多的艺术家就会产生一个非常
简化的思维——“去故意碰撞社会规则”。对此,葛宇路
保持自己的怀疑。
出门去按腿前,葛宇路的朋友来了消息说九月会发一枚
火箭上太空,问他要不要把《葛宇路》的那块路牌送上
去,他决定试试跟收走路牌的街道办聊聊这件事:“说
不定有的聊,因为他们是绝对不会还给我的,也许他们
宁愿把它送到外太空也不愿意给我。”